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:未來五年的改革發展,必將建之于迅速上升的綜合國力、漸入人心的科學發展理念、走向縱深的改革開放進程,以及日益復雜的內外環境基礎之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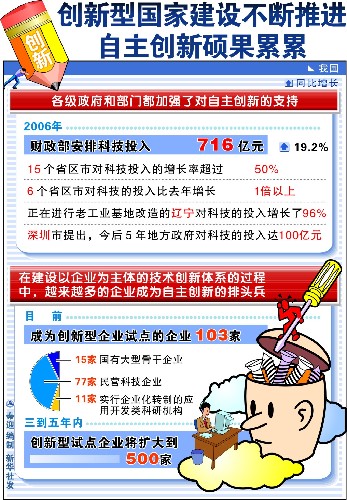
走過高速成長的五年,中國發展再次站到新的歷史起點。新的歷史起點都包括哪些內容,其對于我們今后發展意味著什么,無疑對更好地把握未來至關重要。
就此,《瞭望》新聞周刊深入采訪了長期從事改革發展研究的常修澤教授、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教授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立群研究員、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專家學者,在此基礎上,形成以下四點共識。
起點之一:五年翻番的GDP總量
五年來翻了一番的GDP總量,使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。這一起點,既為我們提供了轉型期豐富的調控經驗與教訓,又為解決國內諸多發展難題提供了物質基礎,增強了發展的抗風險能力;同時也成為中國冷靜判斷自身與世界關系的重要基點。
2001年,中國的GDP總量不到11萬億元;而2007年,這一標志著國家綜合實力的數字將超過23萬億元。五年間翻一番的GDP總量,既建之于上一屆政府打下的堅實基礎,又與新一屆政府五年來“頗有心得”的宏觀調控密不可分。事實上,能將一根高速增長的曲線連續四年穩定在10%左右,在中國29年的改革發展歷史中亦屬罕見。
站在這一新的起點,我們擁有了駕馭未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經驗,積累了遠遠難于成熟市場經濟體的轉型期調控心得,比如“適時適度”,比如“有保有壓”,比如市場、法律和行政等多種手段的靈活運用等等;與此同時,如何在流動性過剩與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宏觀調控,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,還需在今后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。
站在這一新的起點,中國發展的抗風險能力極大增強,并在解決國內諸多發展問題時,有了遠勝于昔的物質基礎:比如為國有商業銀行海外上市提供的改制資金支撐;每年多達500億元的貧困生資助體系建設;以及2007年已覆蓋全國80%縣市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等;但與此同時,如何在新的物質平臺上平衡百姓更多的期待,如何平衡增長波動與福利剛性增長之間的矛盾,以避免超越發展階段的過高需求,也成為當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。
而由經濟總量變動引發的中國與世界關系變動,更將成為未來五年中國發展最重要的考量因素。
起點之二:初步構建的和諧框架
科學發展觀的確立與四年的實踐探索,不僅使“以人為本”、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”等理念漸入人心,同時也成為未來諸多改革的出發點和約束條件;而四年的改革實踐,迄今已初步搭建起涉及農村醫療、貧困生教育、低收入者住房等多重基本保障體系。
以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“科學發展觀”為起點,中國的改革發展開始進入不只追求“速度與數量”,同時更加注重“協調性與質量”的階段。改革領域也從經濟體制向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領域拓展。這既是中國29年市場化取向改革至今的自然延伸,也是對十六大“建設全面小康社會”目標的繼承和發揚。
踐行四年,無論是經濟自身的質量與協調性、還是經濟與外部的協調性,都邁上了新的臺階:宏觀經濟連續四年保持10%左右的穩定增長、企業微觀效益連年大幅回升;而連續四個“一號文件”發出的強烈“惠農”信號、“新農合”在中國農村的迅速推進、貧困生救助體系、保障性住房的高調登場等,則充分地展示了全新發展理念的現實生命力。
也正因此,頗具影響的西班牙雙月刊《對外政策》在列數中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優劣勢時,并不諱言以下兩點,即“健康的宏觀經濟指數和日益細致的經濟政策,使中國得以保持合理的宏觀經濟增速;而社會指標的迅速改善,使政府具有一定的威望。”
毋庸諱言,剛剛“破題起步”的科學發展觀實踐探索,也將面臨下一步發展的諸多挑戰。
首先是經濟自身的協調性仍有較大提升空間。目前經濟增長還存在過多依賴投資,過多依賴出口等特點;而過度投資與出口的背后,則是中國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和創新匱乏問題;粗放的增長方式與資源環境日益尖銳的矛盾,很可能成為下一步發展的巨大約束。
從這個意義上說,深入到體制機制和政績評價體系層面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,成為科學發展觀繞不開的實踐路徑。
其次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。盡管三年來出臺了大量富有針對性的社會發展舉措,但綠色GDP考核體系的一拖再拖,區域、行業、城鄉三大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;節能減排的環境掣肘,以及必須與增加投入配套進行的體制變革一再延遲,都成為下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難題。
這一切的背后,則是新起點上如何平衡“公平與效率”、如何協調“增長的好與快”、如何讓“民生”獲得真正的體制機制解決保障,而非廉價的喝彩與不可持續的拍腦袋決策等諸多難題。
此前的發展實踐一再提醒我們,要讓發展溫暖人心,改革不僅不能回頭,還必須以解決體制性、機制性問題為重點,走出經濟體制,向政治體制、社會體制等更深廣的領域拓展。

